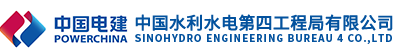一碗漿水寄鄉愁 |
|
|
|
|
辦公室的風扇卷著熱浪呼呼打轉,我總忍不住望向云飄來的方向。腸粉的滑、福鼎肉片的鮮、梅菜扣肉的香,早已成了福建日常的味覺注腳,可舌尖上那點空落落的感覺,總在悶熱的午后悄悄冒頭——是想念老家的漿水了。 那天加班到很晚,回宿舍對著外賣軟件劃了半天,忽然想起母親的漿水飯。酸香混著麥香漫過鼻尖,澆在面上的漿水順著面條滑進喉嚨,配著虎皮辣椒的焦辣、土豆絲的脆甜,暑氣“嗖”地就散了,連帶著心里的躁也平了。 西北人夏天離不得漿水,甘肅人尤甚。開春苜蓿剛探綠芽,母親就會念叨:“該窩漿水了。”新鮮苜蓿窩出的漿水最是清靈,她總說:“菜要洗到根須都發亮,缸得晾到一點潮氣都沒有,封缸時布要扎得密不透風,漿水才肯鮮靈。”她蹲在灶臺前洗菜的樣子,缸沿上水珠滾落的聲音,如今想起來都帶著草木的清潤。 老家的清晨總裹著三弦的調子。奶奶生前愛聽河州賢孝,《韓起功抓兵》里“河州城頭月昏黃”的蒼涼唱腔剛起,廚房就傳來母親搟面條的“咚咚”聲,節奏里裹著火爐升起的炊煙,把鄉愁暖得軟軟的。我總趁母親不注意,溜進廚房掀開漿水缸蓋,舀一勺酸津津的漿水直灌下去,冰涼涼的酸勁兒從舌尖竄到胃里,偷來的快樂比什么都甜。 廚房不大,陽光斜斜切進來時,虎皮辣椒的焦香正和漿水的酸鮮撞個滿懷。母親把搟好的面條下進沸水,白霧騰起的瞬間,仿佛又看見她站在灶臺前,圍裙上沾著面粉,眼里盛著整個夏天的安寧。 原來舌尖那點空缺,從來不是少了一味調料。是想念母親窩漿水時的認真,是懷念偷喝漿水時的雀躍,是記掛著那方小廚房里,永遠等你回家的煙火氣。 直到前幾天從網上下單買了幾袋漿水來,急忙拆開,學著記憶里的樣子切了虎皮辣椒,煮了面條,再把漿水“嘩啦”一聲澆進去。熱氣騰騰的模樣瞧著有幾分像了,可筷子剛夾起面條,心里就空落落的——這味道,終究是差了點什么。 這袋網購的漿水,酸得太過利落,像缺了段勾連記憶的引子。它勾不起母親蹲在院里擇苜蓿的樣子:指尖掐掉黃葉時,總會念叨“這芽子嫩,窩漿水才夠勁”;也想不起她和奶奶封缸時的講究,兩人總說“脾氣較真的人封的口,漿水才會酸得綿厚”;更帶不來那塊磨得掉漆的磁帶音響——那是奶奶用了半輩子的物件;還有我偷喝漿水被撞見時,奶奶嗔怪“涼東西少喝”,轉身卻往我碗里多舀兩勺的溫柔。 原來那碗漿水的味道,從來不是單一的酸。它是苜蓿葉上沾著的晨露,是母親指尖蹭過的泥土香,是老缸里沉淀的歲月,是三弦聲里漫進廚房的河州賢孝,更是千里之外那盞永遠為你亮著的燈。缺了這些,再像的酸香,也填不滿心里那個裝著鄉愁的窟窿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